作者:不吃蛋炒饭
2025/09/20 发布于第一会所
字数:8926
第三十七章 妄念
正月十六,寒风料峭。
姜青麟一行踏上了返回泸州的路途。
队伍堪称精锐:贴身侍卫八人,四个锦衣卫,四个禁卫军,皆是筑基期好手;
这次派跟随他的是锦衣卫都督杨静,元婴初期修为;还有四年前袭粮一役崭露头
角,如今已升任统领的成洪,金丹后期。
这支护卫力量,足以应对路途上可能的大半风险。
姑姑姜芷一身霜色劲装,策马行在他身侧稍前,清冷孤绝,仿佛一柄出鞘的
寒剑,自清晨出发便未与姜青麟说过一句话。
临行前,姜青麟将精心绘制的画卷分送了出去。
给李清秋的,是幼时她将他抱在膝上「渡气」亲吻的画面,旖旎中带着追忆;
给赢莹的,是秘境中那背着她的瞬间,炽热而私密;给姜湘钰的,则是雪夜小亭
灯火阑珊处的深情凝望,含蓄而隽永。
他怀中储物匣里还藏着几幅,预备着给青云岛那位和远在紫云山的佳人。
一路疾行,马蹄踏碎官道上的薄冰。
压抑的气氛在队伍中弥漫,连杨静这等老成持重之人也察觉异样,目不斜视。
夕阳熔金,染红天际时,队伍终于抵达一处驿站。
晚膳席间,姜芷依旧沉默,只用清冷的目光扫过殷勤布菜的姜青麟,便径自
起身,霜袖微拂,独自回了上房。
姜青麟看着她消失在楼梯口的背影,无奈地捏了捏眉心。
指节在桌面上轻轻叩击,心中已有了计较。
夜色渐浓,驿站喧嚣渐息。
姜青麟悄无声息地摸到姜芷房外,指尖轻轻一推——门扉果然应手而开,未
曾落闩。
他闪身入内,反手将门掩上。
房内只燃着一盏孤灯,光线昏黄。
姜芷盘膝坐于榻上,双眸紧闭,周身笼罩着一层若有若无的冰寒剑意,显然
正在调息。
听到门响,她长睫微颤,缓缓睁开眼。
看清来人,她清冷的眸底掠过一丝极快的心慌,随即被强行压下,化作更深
的冰霜,声音如同碎玉击冰:「你来做什么?」
姜青麟厚着脸皮凑到榻边坐下,脸上堆起讨好的笑,手却极其自然地覆上她
搁在膝上的柔荑:「姑姑还在为那晚的事生气呢?」他指腹在她细腻的手背上轻
轻摩挲。
姜芷指尖一颤,想抽回手,却被他五指趁机穿过指缝,紧紧扣住。
她挣了一下未果,索性别过脸去,只留给他一个线条优美的冰冷侧颜和微微
泛红的耳根,鼻腔里发出一声极冷的轻哼:「别碰我!去找你的小姨,寻我作甚?」
姜青麟心知此刻绝不能接这话茬。
他手臂一伸,从背后将她温软的身子整个圈进怀里,下颌亲昵地抵在她肩窝,
灼热的呼吸故意喷洒在她敏感的耳廓,声音低沉带着撒娇般的磁性:「姑姑~ 」
这一声唤得百转千回,热气钻进耳蜗,激得姜芷身子不由自主地一软。
他另一只手也没闲着,从储物法宝中取出一卷画轴,在她眼前徐徐展开。
画面上,是霜华峰顶,寒潭碎冰!年幼的姜青麟正决绝地撞向那致命的冰棱,
而姜芷的身影在碎冰寒潮中惊骇回眸,眼神里是撕裂灵魂般的恐惧与绝望!
「你!」姜芷目光触及画中景象,心脏仿佛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寒潭
边那刻骨的恐惧、怀中冰冷小身体的触感、濒临失去的绝望……所有被她强行冰
封的记忆瞬间汹涌回潮!她猛地闭上眼,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和后怕,
「画这个作甚?收起来!」
姜青麟将她搂得更紧,仿佛要将她嵌入自己怀中,温热的唇几乎贴上她冰凉
的耳垂,声音带着抚慰人心的力量:「就是那一刻,姑姑心里……才真正有了我
的位置吧?我永远记得昏迷后第一次睁眼,看到的就是姑姑的眼睛。
从那时起,我就发誓,我的姑姑,我的师尊,要一辈子在我身边。」他的话
语直击姜青麟心中最深的执念——寒潭的恐惧是两人情孽纠缠的根源,也是姜芷
最无法抗拒的软肋。
姜芷心头巨震,暖流与酸涩交织。
她强自镇定,回眸狠狠瞪了他一眼,试图用嗔怒掩饰心底的波澜:「那时你
才多大?就敢存了这等大逆不道的心思?」
姜青麟低笑,手指温柔地将她颊边一缕碎发捋到耳后,指腹若有似无地擦过
她发烫的耳垂:「谁让姑姑生得这般…惊心动魄?还偏要瞒着我身份,日日让我
唤『师尊』,平白惹得徒儿生出许多…不该有的妄念。」
他刻意将「惊心动魄」和「妄念」咬得暧昧。
姜芷被他这直白露骨的话激得脸上红霞更盛,又想起李清秋之事,心头那股
邪火又蹿了上来,那「小姨娘子」的刺又扎了上来,声音更冷:「哼!不该有的
妄念?你连你小姨都…都摆到一张榻上去了!那时我瞒你身份,不过是想让你心
无旁骛,专心剑道!画送到了,你可以走了。」
她试图挣脱他的怀抱,语气带着驱逐的意味。
姜青麟哪肯放手?他敏锐地捕捉到她语气中那挥之不去的醋意,心中反而一
松。
他舌尖忽然探出,极其迅速地在那敏感的耳蜗内壁轻轻舔舐了一下!
「啊!」姜芷猝不及防,如同被电流击中,浑身猛地一颤,一股难以言喻的
酥麻瞬间从耳蜗窜遍全身!
久旷的身体被这熟悉的挑逗瞬间点燃,腿心深处竟不受控制地沁出一股温热
的湿意,亵裤内一片泥泞。
她羞愤交加,声音都变了调:「姜青麟!你放肆!」
姜青麟感受到怀中娇躯的瞬间绵软和轻颤,嘴角勾起得逞的笑意,低沉的声
音带着洞悉一切的蛊惑:「姑姑若真不想我进来,为何…不锁门呢?」他灼热的
气息持续烘烤着她脆弱的耳根。
姜芷被他戳中心事,又气又急,强辩道:「我…我不过是在调息入定,想着
稍后再去落闩!哪想到你这登徒子如此胆大包天,竟敢…竟敢擅闯!」
话虽如此,她的挣扎却显得绵软无力。
「哦?是吗?」姜青麟轻笑,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
他修长的手指轻轻勾起她精巧的下巴,强迫她转向自己,目光灼灼地锁住她
泛着水光的眸子,「姑姑,我想你了。」
「得寸进尺!你唔……」姜芷的斥责被骤然覆下的滚烫唇瓣堵了回去。
姜青麟的舌头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道,轻易撬开她微弱的抵抗,长驱直入,精
准地捕捉到那条试图躲闪的香软小舌,霸道地纠缠吮吸。
同时,他扣住她手腕的大手松开一只,隔着衣料,精准地覆上她胸前那高耸
饱满的峰峦,掌心带着灼人的热度,用力揉捏起来!饱满的乳肉在他掌下变形,
顶端敏感的蓓蕾在布料摩擦下迅速挺立。
「嗯……」一声压抑的低吟从两人纠缠的唇齿间逸出。
姜芷象征性地推拒着他作恶的手,力道却软得可怜。
那只大手得寸进尺,灵巧的指尖隔着薄薄的衣料,精准地找到那已然硬挺的
乳尖,时轻时重地捻弄、拨挑。
另一只原本扣着她手腕的手也悄然滑下,目标明确地探向她腿心那早已泥泞
一片的饱满耻丘,隔着衣物精准地覆盖在她腿心那微微隆起的柔软丘壑上,用力
地上下揉按、画圈。
那只在她腿心作乱的手显然已不满足于隔靴搔痒。
它灵巧地向下探去,钻入她的裤口,轻易挑开早已濡湿的内裤边缘,两根带
着薄茧的手指直接触碰到那两片微微开合的湿热花瓣,精准地找到了那颗已然充
血挺立的娇嫩阴蒂,用指腹轻轻刮蹭、揉弄。
「嗯哼……」三处敏感地带同时遭受如此精准而热烈的侵袭,姜芷脑中「嗡」
的一声,残存的理智如同风中残烛,瞬间摇摇欲灭。
眼中清冷的冰霜迅速被迷离的水雾取代,情欲的潮红从脸颊蔓延至脖颈。
身体深处涌出的热流更加汹涌,她无助地在他怀中扭动,喉间溢出破碎的嘤
咛:「不…要…嗯…」
姜青麟适时地放开她被吮吸得红肿的唇瓣,唇分时拉出一道淫靡的银丝。
他抽出在她腿间作乱的手,故意在她迷蒙的眼前缓缓张开五指——指尖上沾
满了晶莹黏腻的透明爱液,在昏黄的灯光下反射着淫靡的光泽。
「不要什么?姑姑?」他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情欲和戏谑,将那沾满她蜜
液的手指凑近鼻端,深深嗅了一下。
姜芷呼吸一窒,被他这充满占有欲和羞辱意味的动作刺激得浑身发烫,巨大
的羞耻感让她猛地闭上双眼,如同受惊的鸵鸟般将滚烫的脸颊埋进他胸膛,再不
敢看他一眼,也失去了所有言语的能力。
看着她这副羞窘至极又情动难耐的模样,姜青麟心头爱意与欲火交织升腾。
他不再犹豫,一手揽着她绵软的腰肢,一手利落地开始解她的衣带。
姜芷身体一僵,仿佛抓住救命稻草般按住他解衣的手,声音带着一丝慌乱和
哀求:「别…麟儿…会…会被人听见…」
姜青麟轻笑,指尖快速掐了几个繁复的法诀,一道无形的灵力涟漪瞬间扩散
开来,将整个房间笼罩。
隔音禁制已成。
「现在,没人听得见了,姑姑。」他的声音低沉而充满诱惑。
最后的屏障被解除,姜芷认命般松开了手,将脸更深地埋在他颈窝,任由他
施为。
外衫、中衣、长裤被一件件剥落。
最终,一具只着贴身内衣的完美胴体暴露在昏黄的灯光下:饱满傲人的双峰
被一件精致的黑色蕾丝胸衣紧紧包裹,深邃的沟壑和雪白的乳肉边缘引人遐想;
同色的蕾丝内裤勾勒出饱满耻丘的完美形状,腿心处的布料已被深色的湿痕浸透,
散发出靡靡甜香;一双修长笔直的玉腿裹着薄如蝉翼的黑色丝袜,丝袜顶端精致
的蕾丝花边深深勒进丰腴圆润的大腿肉中,勒出一道道诱人的凹陷。
清冷仙姿与极致诱惑的碰撞,瞬间点燃了姜青麟所有的理智。
他眼中燃起炽热的火焰,俯身在她滚烫的脸颊上重重啄了一口,声音带着浓
重的欲念和促狭:「姑姑…这身打扮…特意为我准备的?嗯?连裤子里面…都套
着丝袜?」他粗糙的指腹隔着丝袜,在她大腿内侧敏感处暧昧地摩挲。
姜芷身体又是一颤,羞得无地自容,嘴硬道:「胡…胡说!只是…只是今日
觉得有些凉,随手…随手拿的…」声音却虚软无力。
看着她口是心非的娇羞模样,姜青麟只觉可爱至极,下腹早已坚硬如铁的欲
望再也无法忍耐。
他迅速褪尽自身衣物,露出精壮健硕的身躯,翻身上榻,挤入她双腿之间。
他双手握住她纤细的脚踝,略一用力便将她双腿大大分开。
那早已泥泞不堪的蕾丝内裤被轻易剥下,挂在另一只脚踝上。
神秘幽谷再无遮掩:粉嫩的花瓣因情动而微微张开,不断沁出晶莹的爱液,
顶端那颗小巧的珍珠已然充血挺立,在灯光下诱人采撷。
姜青麟喉结滚动,目光灼热得几乎要将她融化。
他俯下身,灼热的呼吸尽数喷洒在那片湿漉漉的羞耻之地。
姜芷感受到腿心传来的热气,心头一紧,看清他的意图,慌乱地并拢双腿,
声音带着惊恐的颤抖:「你…别…麟儿!那里…脏…」
「脏?」
姜青麟低笑,鼻尖亲昵地蹭了蹭她柔软的耻丘,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虔诚,
「姑姑是九天仙子,早已无垢无尘,怎会脏?」
话音未落,他竟伸出舌尖,对着那微微翕张的花瓣中心,极其迅速地、带着
挑逗意味地舔了一下!
「呀!」强烈的刺激如同电流窜过脊椎,姜芷惊叫出声,双手下意识地抓住
他的头发,不知是想推开还是按得更深。
姜青麟的攻势却已展开。
他灵活的舌尖如同最灵巧的笔,时而沿着两片娇嫩的花瓣边缘细细勾勒,时
而卷住顶端那颗硬挺的肉珠,或轻吮慢吸,或用舌尖快速拨弄、打转。
每一次舔舐都精准地撩拨着她最敏感的神经。
「嗯…麟儿…别…那里…嗯…啊…」姜芷的身体在他唇舌的侍奉下剧烈颤抖,
双腿时而绷直时而蜷曲,脚趾在丝袜中无助地蜷缩。
从未体验过的极致快感如同潮水般将她淹没,理智彻底溃散,只剩下破碎的
呻吟。
第三十八章不奉陪?
感受到她花穴的剧烈收缩和涌出的更多蜜液,姜青麟的舌尖转移阵地,抵住
那早已湿滑泥泞的穴口,用力向里一顶,整条灵活的舌头便钻了进去!
他模仿着交合的节奏,在紧致湿滑的肉径内快速进出、搅动、舔舐着内壁敏
感的褶皱。
「啊——!麟儿…不…要…嗯…啊…不行了…我…我要…来了…你…你…嗯哼…」
姜芷的呻吟陡然拔高,带着崩溃般的哭腔。
双腿猛地死死夹紧姜青麟的头,腰肢失控地向上拱起,双手死死抓住他的头
发,花穴深处传来一阵剧烈的痉挛!
一股滚烫粘稠、带着独特馥郁香气的阴精猛地从翕张的花心激射而出!部分
被姜青麟贪婪地吞咽下去,更多的则喷溅在他专注的脸上、鼻尖,甚至胸膛。
直到她痉挛的浪潮渐渐平息,身体如同被抽空般软倒在榻上,姜青麟才缓缓
抬起头。
他舔了舔唇边残留的晶莹,看着身下玉体横陈、眼神迷离涣散、大口喘息的
姜芷,胯下的巨物早已怒张贲张,紫红色的龟头油亮渗液。
他再也无法忍耐,双手握住她纤细的腰肢向下一拉,早已坚硬如铁的肉茎抵
住那依旧微微开合、汁水淋漓的花穴入口,腰身猛地向前一挺!
「呃啊——!」伴随着姜芷一声短促而满足的痛吟,粗长滚烫的巨物瞬间撑
开层层叠叠的媚肉,齐根没入!龟头狠狠撞上娇嫩敏感的宫口软肉,带来一阵直
达灵魂深处的酥麻!熟悉的、销魂蚀骨的紧致包裹感瞬间绞紧了姜青麟的神经,
他闷哼一声,差点当场缴械。
姜芷只觉整个身体都被那凶器彻底贯穿、填满,破瓜之痛早已远去,取而代
之的是被彻底占有的满足和灭顶的快感。
她双手无力地攀上他宽阔的脊背,双腿本能地缠上他精壮的腰身,迷离的水
眸望着他因情欲而显得格外俊朗深邃的脸庞,红唇微张,溢出破碎的呻吟:「嗯
…嗯…太…太涨了…慢…慢些…嗯…啊…」
姜青麟俯下身,含住她微张的唇瓣又是一阵深吻,同时,双手毫不客气地扯
下那碍事的黑色蕾丝胸罩,让那对雪白浑圆的玉兔彻底弹跳而出!下身却开始由
缓至急地抽送起来。
每一次退出都带出大量混合着爱液的湿滑汁液,每一次深入都凶狠地直抵花
心,龟头重重碾磨着宫口那敏感的软肉,发出沉闷的「噗叽」声。
他一手握住一团饱满的软肉,用力揉捏抓握,感受着惊人的弹性和分量,指
缝精准地夹住顶端早已硬如石子的嫣红蓓蕾,用力夹紧、揉搓。
姜芷的呻吟尽数被吞入他口中。
胸前敏感点和下体同时遭受着最猛烈的攻击,快感如潮水般层层叠加,几乎
要将她淹没、撕裂。
她只能无助地攀附着他,承受着他狂风暴雨般的侵占:「嗯…嗯…不…要…麟
…儿慢慢…点…啊…啊…」
「啪!啪!啪!」结实的小腹撞击在饱满耻丘上的声音在隔音禁制内清晰回
响,混合着两人粗重的喘息和姜芷越来越无法压抑的媚吟。
「嗯…啊…麟儿…好…好深…顶…顶到了…嗯嗯…啊…」姜芷在他身下婉转承欢,
清冷的容颜染满情欲的红晕,随着他越来越快的撞击而摇晃。
姜青麟放开她被吻得红肿的唇,身下动作毫不停歇,粗喘着在她耳边宣告:
「姑姑…师尊…以后都给我…好不好?」
姜芷神志昏沉,被顶撞得语不成调:「嗯…嗯…逆…逆徒…你…休…想…嗯…哼
…」
姜青麟看着她动情至深的模样,眼中闪过一丝炽热的疯狂。
他猛地抽出深埋的肉茎,在姜芷茫然又带着一丝空虚的嘤咛中,大手握住她
的纤腰,不由分说地将她翻转过去,让她背对自己跪趴在榻上。
「啊!你…做什么?!」骤然改变的体位让姜芷惊呼出声,巨大的羞耻感瞬
间席卷了她!圆润挺翘的雪臀高高撅起,腿间那片湿漉漉、微微红肿的花瓣和不
断收缩的穴口,甚至后方那朵羞涩的菊蕾,都毫无遮掩地暴露在身后男人的目光
之下!那挂在脚踝上的黑色蕾丝内裤和勒进腿肉的丝袜花边更添淫靡。
她羞愤欲绝,挣扎着想回头。
「姑姑…」姜青麟的声音沙哑得可怕,双手握住她纤细的腰肢向后一拉,滚
烫坚硬的龟头再次精准地抵住那翕张的穴口,腰身猛地发力,再次凶狠地贯穿到
底!这个姿势入得更深,每一次顶撞都仿佛要凿穿她的身体,直捣花心最深处!
「啊——!」猝不及防的深顶让姜芷发出一声近乎哭泣的尖叫,双手死死抓
住身下的锦褥,指节因用力而泛白。
这个羞耻的姿势带来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快感如同海啸般将她彻底吞没。
「嗯…啊…太深了…麟儿…轻…轻点…嗯哼…不行…要…」她扭动着腰肢,
似拒还迎,破碎的呻吟带着哭腔。
姜青麟哪里还听得进去?他一手固定住她不堪一握的腰肢,一手覆上那随着
撞击而剧烈晃动的饱满臀峰,用力揉捏抓握,感受着惊人的弹性和滑腻。
身下抽插的速度和力道再次攀升,每一次撞击都带着要将她揉碎的凶狠,龟
头死命地研磨、冲撞着那翕张的娇嫩花心!
「嗯…啊…啊…太深了…麟儿…轻…轻点…嗯…嗯哼…不行了…又要…又要来了…」
姜芷感觉自己被抛上了云端,身体深处的酸麻感积聚到了顶点,灵魂都在颤栗。
就在她濒临爆发的边缘,姜青麟猛地松开她的腰肢,双手抓住她纤细的手腕,
反剪着向后用力拉起!这个姿势让她被迫高高挺起胸膛,腰肢弓起一个惊心动魄
的弧度,臀瓣翘得更高,承受着更加深入、更加猛烈的冲击!
「姑姑!师尊!都给你…都射给你!」姜青麟低吼着,身下冲刺如同狂风暴
雨,每一次都狠狠凿进最深处,龟头死死抵着花心研磨。
「啊——!麟儿…嗯啊…齁嗯…嗯…啊…」姜芷被这极致深入的顶弄和手腕被
反剪的羞耻感刺激得语无伦次,巨大的快感如同电流击穿了她所有的意识。
就在这瞬间,姜青麟腰眼传来灭顶的酸麻,低吼一声,将肉茎死死钉入花穴
最深处,滚烫的精液如同开闸的怒洪,强劲地喷射而出,狠狠冲刷在娇嫩的宫口
软肉上!
「呃啊——!」滚烫的浇灌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姜芷的身体猛地向上反弓到
极致,发出一声高亢到失声的尖叫!花穴内层层媚肉疯狂地痉挛、绞紧,如同无
数张小嘴死死咬住深入体内的凶器,贪婪地吮吸榨取!一股更加汹涌滚烫的阴精
随之喷薄而出,混合着他的精华,在两人紧密交合处肆意流淌。
极致的痉挛持续了许久,姜芷才如同被抽去了所有骨头般瘫软下来,浑身香
汗淋漓,眼神涣散失焦,红唇微张,一缕晶莹的涎液顺着嘴角滑落,只剩下细碎
无意识的抽噎。
姜青麟也喘息着趴伏在她汗湿的玉背上,感受着她体内媚肉余韵未消的绞吸,
许久才缓缓退出。
「啵…」一声淫靡的水响,带出更多混合着白浊的粘腻汁液。
姜芷敏感的身体又是一颤。
姜青麟取过干净的布巾,仔细地为她擦拭腿间狼藉。
看着她那微微红肿、兀自开合、不断有浓白的精液混着蜜液缓缓淌出,顺着
腿根流下。
这淫靡的画面刺激得他险些再次失控。
他强动作轻柔地为她清理下身狼藉。
清理完毕,才将她绵软的身子翻转过来,紧紧拥入怀中。
姜芷早已疲惫不堪,闭着眼装睡,长长的睫毛却还在微微颤抖。
姜青麟爱怜地在她汗湿的额发上印下一吻,手臂收紧,将她牢牢锁在怀中,
感受着她平稳下来的呼吸和心跳,满足地闭上了眼。
怀中传来平稳的呼吸声,姜芷才缓缓睁开眼。
借着微弱的烛火,凝视着他沉睡中依旧俊朗的侧颜,心中翻涌着复杂难言的
情绪,最终化为一丝无奈的甜蜜。
她无声地叹了口气,身体不自觉地向他怀里更深处依偎过去。
翌日清晨。
姜青麟醒来时,怀中已空。
姜芷背对着他站在窗边,正将霜色外袍的最后一丝褶皱抚平。
晨光勾勒出她清冷孤绝的侧影,仿佛昨夜那场抵死缠绵只是幻梦。
「还不快起?杨静他们都在外面候着了。」她回眸瞥了他一眼,语气恢复了
惯有的清冷,似乎比平日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只是眼波流转间,还残留着
一丝不易察觉的慵懒媚意。
姜青麟连忙起身穿衣,随口应道:「嗯,知道了。」
姜芷望向窗外官道,黛眉微蹙,似乎在计算行程:「照此脚程,抵达泸州,
再折返临淄…约莫两月足矣。」
姜青麟系腰带的手猛地一顿,心虚地「嗯」了一声,声音含糊:「两个月
…怕是…回不来。」
姜芷疑惑地转身,清冷的目光带着审视落在他脸上:「此去泸州路途虽远,
但御风行舟或全力策马,两月往返绰绰有余。即便绕道去青丘提亲,时间也尽够
了。你磨蹭什么?」
姜青麟头皮发麻,不敢直视她的眼睛,目光游移地盯着地板,手指无意识地
蜷缩着,声音越来越小,几乎含在嘴里:「嗯…那个…除了青丘…还得去趟青云
岛…还有…紫云山那边…也得…」最后几个字彻底没了声息。
房内瞬间陷入死寂。
姜芷脸上的血色「唰」地一下褪尽,随即又被汹涌的怒火烧得通红!她死死
盯着姜青麟,清冷的眸子里瞬间凝结出万载寒冰,声音却平静得可怕,一字一顿:
「当、初、在、驿、站、你、是、如、何、对、我、说、的?『也就见过几面』,
『只是招待』,『哪里及得上姑姑』?」
她每说一个字,身上的寒气便重一分,元婴期的威压不受控制地弥漫开来,
室内的温度骤降!
「姜青麟!你好!你很好!」她声音陡然拔高,带着被欺骗的愤怒和心寒。
怒火攻心之下,她一步上前,抬手就对着姜青麟的脑袋狠狠拍了几下!「啪!
啪!」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清晨格外刺耳。
越想越气,她抬脚对着他光裸的胸膛就是一脚踹去!
「砰!」姜青麟猝不及防,被这一脚蕴含的巨力拍得闷哼一声,踉跄后退数
步,后背重重撞在墙壁上。
姜芷看也不看他,眼中只剩下被欺骗的怒火和冰冷的失望,霜袖猛地一拂,
带起凛冽寒风:「哼!你自己去提你的亲吧!本宫不奉陪了!」
房门被一股狂暴的气劲猛地撞开,又在她身影消失后「砰」地一声重重关上,
震得门框嗡嗡作响,只留下满室冰冷和一脸苦笑的姜青麟,以及空气中尚未散尽
的…昨夜旖旎又荒诞的气息。
驿站大堂
杨静、成洪等人早已整装待发,肃立等候。
忽见长公主姜芷面罩寒霜,疾步而出,周身散发的低气压让整个驿站大堂的
温度骤降!
众人心头一凛,慌忙躬身行礼,大气不敢出:「参见长公主!」
姜芷看也未看他们,径直向外走去。
行至门口,她的脚步猛地一顿!
一股无形的、令人窒息的威压瞬间笼罩全场!杨静等人只觉得背脊发凉,冷
汗瞬间浸透内衫,头颅垂得更低,几乎要埋进胸膛里。
片刻,那冰冷刺骨的声音才缓缓传来,如同寒冰碎裂:「尔等……随他去吧。
剑宗有急务,本宫先行一步。」说罢,再次举步欲走。
就在杨静等人刚松半口气时,姜芷的脚步竟在门槛处再次顿住!
所有人的心瞬间又提到了嗓子眼!
这一次,那清冷的声音缓和了些许,虽依旧带着疏离,却少了几分刺骨的寒
意:「……护好殿下。」
杨静如蒙大赦,一个箭步跨出队列,单膝跪地,声音洪亮而恭敬:「属下遵
命!恭送长公主!」直到那袭清冷的身影彻底消失在驿道尽头,他才心有余悸地
缓缓起身,与同样面色发白的成洪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苦笑。
看来殿下……又捅了大篓子了。
……分割线……
第二卷结卷了,感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第三卷是会渐渐完善人设主角的性
格,让大伙有些清楚认知此书的世界观。
第二卷主要的女主就是姑姑和小姨,还有姐姐和岳母的戏份,不知道大家喜
不喜欢这四个角色。
希望能让你们喜欢。
在这里回复一下这句评价:(在这里留言也不知道这个作者能不能看见,如
果能看见的话,我建议作者还是别写了,这人物跟个背台词的木偶似的,剧情也
是完全没有的,真的都不如ai自己写呢)
「感谢你的阅读和评价。
我写这本书纯粹是『为爱发电』,免费分享给所有愿意看的朋友。
它可能不完美,但每一个字都是我用心写的成果,它对我而言意义非凡。
刘备文很多,有无数优秀的作品可供选择。
如果这个故事确实不合你的口味,你拥有随时离开的自由,祝你能找到你喜
欢的书。」
2025/09/20 发布于第一会所
字数:8926
第三十七章 妄念
正月十六,寒风料峭。
姜青麟一行踏上了返回泸州的路途。
队伍堪称精锐:贴身侍卫八人,四个锦衣卫,四个禁卫军,皆是筑基期好手;
这次派跟随他的是锦衣卫都督杨静,元婴初期修为;还有四年前袭粮一役崭露头
角,如今已升任统领的成洪,金丹后期。
这支护卫力量,足以应对路途上可能的大半风险。
姑姑姜芷一身霜色劲装,策马行在他身侧稍前,清冷孤绝,仿佛一柄出鞘的
寒剑,自清晨出发便未与姜青麟说过一句话。
临行前,姜青麟将精心绘制的画卷分送了出去。
给李清秋的,是幼时她将他抱在膝上「渡气」亲吻的画面,旖旎中带着追忆;
给赢莹的,是秘境中那背着她的瞬间,炽热而私密;给姜湘钰的,则是雪夜小亭
灯火阑珊处的深情凝望,含蓄而隽永。
他怀中储物匣里还藏着几幅,预备着给青云岛那位和远在紫云山的佳人。
一路疾行,马蹄踏碎官道上的薄冰。
压抑的气氛在队伍中弥漫,连杨静这等老成持重之人也察觉异样,目不斜视。
夕阳熔金,染红天际时,队伍终于抵达一处驿站。
晚膳席间,姜芷依旧沉默,只用清冷的目光扫过殷勤布菜的姜青麟,便径自
起身,霜袖微拂,独自回了上房。
姜青麟看着她消失在楼梯口的背影,无奈地捏了捏眉心。
指节在桌面上轻轻叩击,心中已有了计较。
夜色渐浓,驿站喧嚣渐息。
姜青麟悄无声息地摸到姜芷房外,指尖轻轻一推——门扉果然应手而开,未
曾落闩。
他闪身入内,反手将门掩上。
房内只燃着一盏孤灯,光线昏黄。
姜芷盘膝坐于榻上,双眸紧闭,周身笼罩着一层若有若无的冰寒剑意,显然
正在调息。
听到门响,她长睫微颤,缓缓睁开眼。
看清来人,她清冷的眸底掠过一丝极快的心慌,随即被强行压下,化作更深
的冰霜,声音如同碎玉击冰:「你来做什么?」
姜青麟厚着脸皮凑到榻边坐下,脸上堆起讨好的笑,手却极其自然地覆上她
搁在膝上的柔荑:「姑姑还在为那晚的事生气呢?」他指腹在她细腻的手背上轻
轻摩挲。
姜芷指尖一颤,想抽回手,却被他五指趁机穿过指缝,紧紧扣住。
她挣了一下未果,索性别过脸去,只留给他一个线条优美的冰冷侧颜和微微
泛红的耳根,鼻腔里发出一声极冷的轻哼:「别碰我!去找你的小姨,寻我作甚?」
姜青麟心知此刻绝不能接这话茬。
他手臂一伸,从背后将她温软的身子整个圈进怀里,下颌亲昵地抵在她肩窝,
灼热的呼吸故意喷洒在她敏感的耳廓,声音低沉带着撒娇般的磁性:「姑姑~ 」
这一声唤得百转千回,热气钻进耳蜗,激得姜芷身子不由自主地一软。
他另一只手也没闲着,从储物法宝中取出一卷画轴,在她眼前徐徐展开。
画面上,是霜华峰顶,寒潭碎冰!年幼的姜青麟正决绝地撞向那致命的冰棱,
而姜芷的身影在碎冰寒潮中惊骇回眸,眼神里是撕裂灵魂般的恐惧与绝望!
「你!」姜芷目光触及画中景象,心脏仿佛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寒潭
边那刻骨的恐惧、怀中冰冷小身体的触感、濒临失去的绝望……所有被她强行冰
封的记忆瞬间汹涌回潮!她猛地闭上眼,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和后怕,
「画这个作甚?收起来!」
姜青麟将她搂得更紧,仿佛要将她嵌入自己怀中,温热的唇几乎贴上她冰凉
的耳垂,声音带着抚慰人心的力量:「就是那一刻,姑姑心里……才真正有了我
的位置吧?我永远记得昏迷后第一次睁眼,看到的就是姑姑的眼睛。
从那时起,我就发誓,我的姑姑,我的师尊,要一辈子在我身边。」他的话
语直击姜青麟心中最深的执念——寒潭的恐惧是两人情孽纠缠的根源,也是姜芷
最无法抗拒的软肋。
姜芷心头巨震,暖流与酸涩交织。
她强自镇定,回眸狠狠瞪了他一眼,试图用嗔怒掩饰心底的波澜:「那时你
才多大?就敢存了这等大逆不道的心思?」
姜青麟低笑,手指温柔地将她颊边一缕碎发捋到耳后,指腹若有似无地擦过
她发烫的耳垂:「谁让姑姑生得这般…惊心动魄?还偏要瞒着我身份,日日让我
唤『师尊』,平白惹得徒儿生出许多…不该有的妄念。」
他刻意将「惊心动魄」和「妄念」咬得暧昧。
姜芷被他这直白露骨的话激得脸上红霞更盛,又想起李清秋之事,心头那股
邪火又蹿了上来,那「小姨娘子」的刺又扎了上来,声音更冷:「哼!不该有的
妄念?你连你小姨都…都摆到一张榻上去了!那时我瞒你身份,不过是想让你心
无旁骛,专心剑道!画送到了,你可以走了。」
她试图挣脱他的怀抱,语气带着驱逐的意味。
姜青麟哪肯放手?他敏锐地捕捉到她语气中那挥之不去的醋意,心中反而一
松。
他舌尖忽然探出,极其迅速地在那敏感的耳蜗内壁轻轻舔舐了一下!
「啊!」姜芷猝不及防,如同被电流击中,浑身猛地一颤,一股难以言喻的
酥麻瞬间从耳蜗窜遍全身!
久旷的身体被这熟悉的挑逗瞬间点燃,腿心深处竟不受控制地沁出一股温热
的湿意,亵裤内一片泥泞。
她羞愤交加,声音都变了调:「姜青麟!你放肆!」
姜青麟感受到怀中娇躯的瞬间绵软和轻颤,嘴角勾起得逞的笑意,低沉的声
音带着洞悉一切的蛊惑:「姑姑若真不想我进来,为何…不锁门呢?」他灼热的
气息持续烘烤着她脆弱的耳根。
姜芷被他戳中心事,又气又急,强辩道:「我…我不过是在调息入定,想着
稍后再去落闩!哪想到你这登徒子如此胆大包天,竟敢…竟敢擅闯!」
话虽如此,她的挣扎却显得绵软无力。
「哦?是吗?」姜青麟轻笑,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
他修长的手指轻轻勾起她精巧的下巴,强迫她转向自己,目光灼灼地锁住她
泛着水光的眸子,「姑姑,我想你了。」
「得寸进尺!你唔……」姜芷的斥责被骤然覆下的滚烫唇瓣堵了回去。
姜青麟的舌头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道,轻易撬开她微弱的抵抗,长驱直入,精
准地捕捉到那条试图躲闪的香软小舌,霸道地纠缠吮吸。
同时,他扣住她手腕的大手松开一只,隔着衣料,精准地覆上她胸前那高耸
饱满的峰峦,掌心带着灼人的热度,用力揉捏起来!饱满的乳肉在他掌下变形,
顶端敏感的蓓蕾在布料摩擦下迅速挺立。
「嗯……」一声压抑的低吟从两人纠缠的唇齿间逸出。
姜芷象征性地推拒着他作恶的手,力道却软得可怜。
那只大手得寸进尺,灵巧的指尖隔着薄薄的衣料,精准地找到那已然硬挺的
乳尖,时轻时重地捻弄、拨挑。
另一只原本扣着她手腕的手也悄然滑下,目标明确地探向她腿心那早已泥泞
一片的饱满耻丘,隔着衣物精准地覆盖在她腿心那微微隆起的柔软丘壑上,用力
地上下揉按、画圈。
那只在她腿心作乱的手显然已不满足于隔靴搔痒。
它灵巧地向下探去,钻入她的裤口,轻易挑开早已濡湿的内裤边缘,两根带
着薄茧的手指直接触碰到那两片微微开合的湿热花瓣,精准地找到了那颗已然充
血挺立的娇嫩阴蒂,用指腹轻轻刮蹭、揉弄。
「嗯哼……」三处敏感地带同时遭受如此精准而热烈的侵袭,姜芷脑中「嗡」
的一声,残存的理智如同风中残烛,瞬间摇摇欲灭。
眼中清冷的冰霜迅速被迷离的水雾取代,情欲的潮红从脸颊蔓延至脖颈。
身体深处涌出的热流更加汹涌,她无助地在他怀中扭动,喉间溢出破碎的嘤
咛:「不…要…嗯…」
姜青麟适时地放开她被吮吸得红肿的唇瓣,唇分时拉出一道淫靡的银丝。
他抽出在她腿间作乱的手,故意在她迷蒙的眼前缓缓张开五指——指尖上沾
满了晶莹黏腻的透明爱液,在昏黄的灯光下反射着淫靡的光泽。
「不要什么?姑姑?」他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情欲和戏谑,将那沾满她蜜
液的手指凑近鼻端,深深嗅了一下。
姜芷呼吸一窒,被他这充满占有欲和羞辱意味的动作刺激得浑身发烫,巨大
的羞耻感让她猛地闭上双眼,如同受惊的鸵鸟般将滚烫的脸颊埋进他胸膛,再不
敢看他一眼,也失去了所有言语的能力。
看着她这副羞窘至极又情动难耐的模样,姜青麟心头爱意与欲火交织升腾。
他不再犹豫,一手揽着她绵软的腰肢,一手利落地开始解她的衣带。
姜芷身体一僵,仿佛抓住救命稻草般按住他解衣的手,声音带着一丝慌乱和
哀求:「别…麟儿…会…会被人听见…」
姜青麟轻笑,指尖快速掐了几个繁复的法诀,一道无形的灵力涟漪瞬间扩散
开来,将整个房间笼罩。
隔音禁制已成。
「现在,没人听得见了,姑姑。」他的声音低沉而充满诱惑。
最后的屏障被解除,姜芷认命般松开了手,将脸更深地埋在他颈窝,任由他
施为。
外衫、中衣、长裤被一件件剥落。
最终,一具只着贴身内衣的完美胴体暴露在昏黄的灯光下:饱满傲人的双峰
被一件精致的黑色蕾丝胸衣紧紧包裹,深邃的沟壑和雪白的乳肉边缘引人遐想;
同色的蕾丝内裤勾勒出饱满耻丘的完美形状,腿心处的布料已被深色的湿痕浸透,
散发出靡靡甜香;一双修长笔直的玉腿裹着薄如蝉翼的黑色丝袜,丝袜顶端精致
的蕾丝花边深深勒进丰腴圆润的大腿肉中,勒出一道道诱人的凹陷。
清冷仙姿与极致诱惑的碰撞,瞬间点燃了姜青麟所有的理智。
他眼中燃起炽热的火焰,俯身在她滚烫的脸颊上重重啄了一口,声音带着浓
重的欲念和促狭:「姑姑…这身打扮…特意为我准备的?嗯?连裤子里面…都套
着丝袜?」他粗糙的指腹隔着丝袜,在她大腿内侧敏感处暧昧地摩挲。
姜芷身体又是一颤,羞得无地自容,嘴硬道:「胡…胡说!只是…只是今日
觉得有些凉,随手…随手拿的…」声音却虚软无力。
看着她口是心非的娇羞模样,姜青麟只觉可爱至极,下腹早已坚硬如铁的欲
望再也无法忍耐。
他迅速褪尽自身衣物,露出精壮健硕的身躯,翻身上榻,挤入她双腿之间。
他双手握住她纤细的脚踝,略一用力便将她双腿大大分开。
那早已泥泞不堪的蕾丝内裤被轻易剥下,挂在另一只脚踝上。
神秘幽谷再无遮掩:粉嫩的花瓣因情动而微微张开,不断沁出晶莹的爱液,
顶端那颗小巧的珍珠已然充血挺立,在灯光下诱人采撷。
姜青麟喉结滚动,目光灼热得几乎要将她融化。
他俯下身,灼热的呼吸尽数喷洒在那片湿漉漉的羞耻之地。
姜芷感受到腿心传来的热气,心头一紧,看清他的意图,慌乱地并拢双腿,
声音带着惊恐的颤抖:「你…别…麟儿!那里…脏…」
「脏?」
姜青麟低笑,鼻尖亲昵地蹭了蹭她柔软的耻丘,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虔诚,
「姑姑是九天仙子,早已无垢无尘,怎会脏?」
话音未落,他竟伸出舌尖,对着那微微翕张的花瓣中心,极其迅速地、带着
挑逗意味地舔了一下!
「呀!」强烈的刺激如同电流窜过脊椎,姜芷惊叫出声,双手下意识地抓住
他的头发,不知是想推开还是按得更深。
姜青麟的攻势却已展开。
他灵活的舌尖如同最灵巧的笔,时而沿着两片娇嫩的花瓣边缘细细勾勒,时
而卷住顶端那颗硬挺的肉珠,或轻吮慢吸,或用舌尖快速拨弄、打转。
每一次舔舐都精准地撩拨着她最敏感的神经。
「嗯…麟儿…别…那里…嗯…啊…」姜芷的身体在他唇舌的侍奉下剧烈颤抖,
双腿时而绷直时而蜷曲,脚趾在丝袜中无助地蜷缩。
从未体验过的极致快感如同潮水般将她淹没,理智彻底溃散,只剩下破碎的
呻吟。
第三十八章不奉陪?
感受到她花穴的剧烈收缩和涌出的更多蜜液,姜青麟的舌尖转移阵地,抵住
那早已湿滑泥泞的穴口,用力向里一顶,整条灵活的舌头便钻了进去!
他模仿着交合的节奏,在紧致湿滑的肉径内快速进出、搅动、舔舐着内壁敏
感的褶皱。
「啊——!麟儿…不…要…嗯…啊…不行了…我…我要…来了…你…你…嗯哼…」
姜芷的呻吟陡然拔高,带着崩溃般的哭腔。
双腿猛地死死夹紧姜青麟的头,腰肢失控地向上拱起,双手死死抓住他的头
发,花穴深处传来一阵剧烈的痉挛!
一股滚烫粘稠、带着独特馥郁香气的阴精猛地从翕张的花心激射而出!部分
被姜青麟贪婪地吞咽下去,更多的则喷溅在他专注的脸上、鼻尖,甚至胸膛。
直到她痉挛的浪潮渐渐平息,身体如同被抽空般软倒在榻上,姜青麟才缓缓
抬起头。
他舔了舔唇边残留的晶莹,看着身下玉体横陈、眼神迷离涣散、大口喘息的
姜芷,胯下的巨物早已怒张贲张,紫红色的龟头油亮渗液。
他再也无法忍耐,双手握住她纤细的腰肢向下一拉,早已坚硬如铁的肉茎抵
住那依旧微微开合、汁水淋漓的花穴入口,腰身猛地向前一挺!
「呃啊——!」伴随着姜芷一声短促而满足的痛吟,粗长滚烫的巨物瞬间撑
开层层叠叠的媚肉,齐根没入!龟头狠狠撞上娇嫩敏感的宫口软肉,带来一阵直
达灵魂深处的酥麻!熟悉的、销魂蚀骨的紧致包裹感瞬间绞紧了姜青麟的神经,
他闷哼一声,差点当场缴械。
姜芷只觉整个身体都被那凶器彻底贯穿、填满,破瓜之痛早已远去,取而代
之的是被彻底占有的满足和灭顶的快感。
她双手无力地攀上他宽阔的脊背,双腿本能地缠上他精壮的腰身,迷离的水
眸望着他因情欲而显得格外俊朗深邃的脸庞,红唇微张,溢出破碎的呻吟:「嗯
…嗯…太…太涨了…慢…慢些…嗯…啊…」
姜青麟俯下身,含住她微张的唇瓣又是一阵深吻,同时,双手毫不客气地扯
下那碍事的黑色蕾丝胸罩,让那对雪白浑圆的玉兔彻底弹跳而出!下身却开始由
缓至急地抽送起来。
每一次退出都带出大量混合着爱液的湿滑汁液,每一次深入都凶狠地直抵花
心,龟头重重碾磨着宫口那敏感的软肉,发出沉闷的「噗叽」声。
他一手握住一团饱满的软肉,用力揉捏抓握,感受着惊人的弹性和分量,指
缝精准地夹住顶端早已硬如石子的嫣红蓓蕾,用力夹紧、揉搓。
姜芷的呻吟尽数被吞入他口中。
胸前敏感点和下体同时遭受着最猛烈的攻击,快感如潮水般层层叠加,几乎
要将她淹没、撕裂。
她只能无助地攀附着他,承受着他狂风暴雨般的侵占:「嗯…嗯…不…要…麟
…儿慢慢…点…啊…啊…」
「啪!啪!啪!」结实的小腹撞击在饱满耻丘上的声音在隔音禁制内清晰回
响,混合着两人粗重的喘息和姜芷越来越无法压抑的媚吟。
「嗯…啊…麟儿…好…好深…顶…顶到了…嗯嗯…啊…」姜芷在他身下婉转承欢,
清冷的容颜染满情欲的红晕,随着他越来越快的撞击而摇晃。
姜青麟放开她被吻得红肿的唇,身下动作毫不停歇,粗喘着在她耳边宣告:
「姑姑…师尊…以后都给我…好不好?」
姜芷神志昏沉,被顶撞得语不成调:「嗯…嗯…逆…逆徒…你…休…想…嗯…哼
…」
姜青麟看着她动情至深的模样,眼中闪过一丝炽热的疯狂。
他猛地抽出深埋的肉茎,在姜芷茫然又带着一丝空虚的嘤咛中,大手握住她
的纤腰,不由分说地将她翻转过去,让她背对自己跪趴在榻上。
「啊!你…做什么?!」骤然改变的体位让姜芷惊呼出声,巨大的羞耻感瞬
间席卷了她!圆润挺翘的雪臀高高撅起,腿间那片湿漉漉、微微红肿的花瓣和不
断收缩的穴口,甚至后方那朵羞涩的菊蕾,都毫无遮掩地暴露在身后男人的目光
之下!那挂在脚踝上的黑色蕾丝内裤和勒进腿肉的丝袜花边更添淫靡。
她羞愤欲绝,挣扎着想回头。
「姑姑…」姜青麟的声音沙哑得可怕,双手握住她纤细的腰肢向后一拉,滚
烫坚硬的龟头再次精准地抵住那翕张的穴口,腰身猛地发力,再次凶狠地贯穿到
底!这个姿势入得更深,每一次顶撞都仿佛要凿穿她的身体,直捣花心最深处!
「啊——!」猝不及防的深顶让姜芷发出一声近乎哭泣的尖叫,双手死死抓
住身下的锦褥,指节因用力而泛白。
这个羞耻的姿势带来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快感如同海啸般将她彻底吞没。
「嗯…啊…太深了…麟儿…轻…轻点…嗯哼…不行…要…」她扭动着腰肢,
似拒还迎,破碎的呻吟带着哭腔。
姜青麟哪里还听得进去?他一手固定住她不堪一握的腰肢,一手覆上那随着
撞击而剧烈晃动的饱满臀峰,用力揉捏抓握,感受着惊人的弹性和滑腻。
身下抽插的速度和力道再次攀升,每一次撞击都带着要将她揉碎的凶狠,龟
头死命地研磨、冲撞着那翕张的娇嫩花心!
「嗯…啊…啊…太深了…麟儿…轻…轻点…嗯…嗯哼…不行了…又要…又要来了…」
姜芷感觉自己被抛上了云端,身体深处的酸麻感积聚到了顶点,灵魂都在颤栗。
就在她濒临爆发的边缘,姜青麟猛地松开她的腰肢,双手抓住她纤细的手腕,
反剪着向后用力拉起!这个姿势让她被迫高高挺起胸膛,腰肢弓起一个惊心动魄
的弧度,臀瓣翘得更高,承受着更加深入、更加猛烈的冲击!
「姑姑!师尊!都给你…都射给你!」姜青麟低吼着,身下冲刺如同狂风暴
雨,每一次都狠狠凿进最深处,龟头死死抵着花心研磨。
「啊——!麟儿…嗯啊…齁嗯…嗯…啊…」姜芷被这极致深入的顶弄和手腕被
反剪的羞耻感刺激得语无伦次,巨大的快感如同电流击穿了她所有的意识。
就在这瞬间,姜青麟腰眼传来灭顶的酸麻,低吼一声,将肉茎死死钉入花穴
最深处,滚烫的精液如同开闸的怒洪,强劲地喷射而出,狠狠冲刷在娇嫩的宫口
软肉上!
「呃啊——!」滚烫的浇灌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姜芷的身体猛地向上反弓到
极致,发出一声高亢到失声的尖叫!花穴内层层媚肉疯狂地痉挛、绞紧,如同无
数张小嘴死死咬住深入体内的凶器,贪婪地吮吸榨取!一股更加汹涌滚烫的阴精
随之喷薄而出,混合着他的精华,在两人紧密交合处肆意流淌。
极致的痉挛持续了许久,姜芷才如同被抽去了所有骨头般瘫软下来,浑身香
汗淋漓,眼神涣散失焦,红唇微张,一缕晶莹的涎液顺着嘴角滑落,只剩下细碎
无意识的抽噎。
姜青麟也喘息着趴伏在她汗湿的玉背上,感受着她体内媚肉余韵未消的绞吸,
许久才缓缓退出。
「啵…」一声淫靡的水响,带出更多混合着白浊的粘腻汁液。
姜芷敏感的身体又是一颤。
姜青麟取过干净的布巾,仔细地为她擦拭腿间狼藉。
看着她那微微红肿、兀自开合、不断有浓白的精液混着蜜液缓缓淌出,顺着
腿根流下。
这淫靡的画面刺激得他险些再次失控。
他强动作轻柔地为她清理下身狼藉。
清理完毕,才将她绵软的身子翻转过来,紧紧拥入怀中。
姜芷早已疲惫不堪,闭着眼装睡,长长的睫毛却还在微微颤抖。
姜青麟爱怜地在她汗湿的额发上印下一吻,手臂收紧,将她牢牢锁在怀中,
感受着她平稳下来的呼吸和心跳,满足地闭上了眼。
怀中传来平稳的呼吸声,姜芷才缓缓睁开眼。
借着微弱的烛火,凝视着他沉睡中依旧俊朗的侧颜,心中翻涌着复杂难言的
情绪,最终化为一丝无奈的甜蜜。
她无声地叹了口气,身体不自觉地向他怀里更深处依偎过去。
翌日清晨。
姜青麟醒来时,怀中已空。
姜芷背对着他站在窗边,正将霜色外袍的最后一丝褶皱抚平。
晨光勾勒出她清冷孤绝的侧影,仿佛昨夜那场抵死缠绵只是幻梦。
「还不快起?杨静他们都在外面候着了。」她回眸瞥了他一眼,语气恢复了
惯有的清冷,似乎比平日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只是眼波流转间,还残留着
一丝不易察觉的慵懒媚意。
姜青麟连忙起身穿衣,随口应道:「嗯,知道了。」
姜芷望向窗外官道,黛眉微蹙,似乎在计算行程:「照此脚程,抵达泸州,
再折返临淄…约莫两月足矣。」
姜青麟系腰带的手猛地一顿,心虚地「嗯」了一声,声音含糊:「两个月
…怕是…回不来。」
姜芷疑惑地转身,清冷的目光带着审视落在他脸上:「此去泸州路途虽远,
但御风行舟或全力策马,两月往返绰绰有余。即便绕道去青丘提亲,时间也尽够
了。你磨蹭什么?」
姜青麟头皮发麻,不敢直视她的眼睛,目光游移地盯着地板,手指无意识地
蜷缩着,声音越来越小,几乎含在嘴里:「嗯…那个…除了青丘…还得去趟青云
岛…还有…紫云山那边…也得…」最后几个字彻底没了声息。
房内瞬间陷入死寂。
姜芷脸上的血色「唰」地一下褪尽,随即又被汹涌的怒火烧得通红!她死死
盯着姜青麟,清冷的眸子里瞬间凝结出万载寒冰,声音却平静得可怕,一字一顿:
「当、初、在、驿、站、你、是、如、何、对、我、说、的?『也就见过几面』,
『只是招待』,『哪里及得上姑姑』?」
她每说一个字,身上的寒气便重一分,元婴期的威压不受控制地弥漫开来,
室内的温度骤降!
「姜青麟!你好!你很好!」她声音陡然拔高,带着被欺骗的愤怒和心寒。
怒火攻心之下,她一步上前,抬手就对着姜青麟的脑袋狠狠拍了几下!「啪!
啪!」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清晨格外刺耳。
越想越气,她抬脚对着他光裸的胸膛就是一脚踹去!
「砰!」姜青麟猝不及防,被这一脚蕴含的巨力拍得闷哼一声,踉跄后退数
步,后背重重撞在墙壁上。
姜芷看也不看他,眼中只剩下被欺骗的怒火和冰冷的失望,霜袖猛地一拂,
带起凛冽寒风:「哼!你自己去提你的亲吧!本宫不奉陪了!」
房门被一股狂暴的气劲猛地撞开,又在她身影消失后「砰」地一声重重关上,
震得门框嗡嗡作响,只留下满室冰冷和一脸苦笑的姜青麟,以及空气中尚未散尽
的…昨夜旖旎又荒诞的气息。
驿站大堂
杨静、成洪等人早已整装待发,肃立等候。
忽见长公主姜芷面罩寒霜,疾步而出,周身散发的低气压让整个驿站大堂的
温度骤降!
众人心头一凛,慌忙躬身行礼,大气不敢出:「参见长公主!」
姜芷看也未看他们,径直向外走去。
行至门口,她的脚步猛地一顿!
一股无形的、令人窒息的威压瞬间笼罩全场!杨静等人只觉得背脊发凉,冷
汗瞬间浸透内衫,头颅垂得更低,几乎要埋进胸膛里。
片刻,那冰冷刺骨的声音才缓缓传来,如同寒冰碎裂:「尔等……随他去吧。
剑宗有急务,本宫先行一步。」说罢,再次举步欲走。
就在杨静等人刚松半口气时,姜芷的脚步竟在门槛处再次顿住!
所有人的心瞬间又提到了嗓子眼!
这一次,那清冷的声音缓和了些许,虽依旧带着疏离,却少了几分刺骨的寒
意:「……护好殿下。」
杨静如蒙大赦,一个箭步跨出队列,单膝跪地,声音洪亮而恭敬:「属下遵
命!恭送长公主!」直到那袭清冷的身影彻底消失在驿道尽头,他才心有余悸地
缓缓起身,与同样面色发白的成洪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苦笑。
看来殿下……又捅了大篓子了。
……分割线……
第二卷结卷了,感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第三卷是会渐渐完善人设主角的性
格,让大伙有些清楚认知此书的世界观。
第二卷主要的女主就是姑姑和小姨,还有姐姐和岳母的戏份,不知道大家喜
不喜欢这四个角色。
希望能让你们喜欢。
在这里回复一下这句评价:(在这里留言也不知道这个作者能不能看见,如
果能看见的话,我建议作者还是别写了,这人物跟个背台词的木偶似的,剧情也
是完全没有的,真的都不如ai自己写呢)
「感谢你的阅读和评价。
我写这本书纯粹是『为爱发电』,免费分享给所有愿意看的朋友。
它可能不完美,但每一个字都是我用心写的成果,它对我而言意义非凡。
刘备文很多,有无数优秀的作品可供选择。
如果这个故事确实不合你的口味,你拥有随时离开的自由,祝你能找到你喜
欢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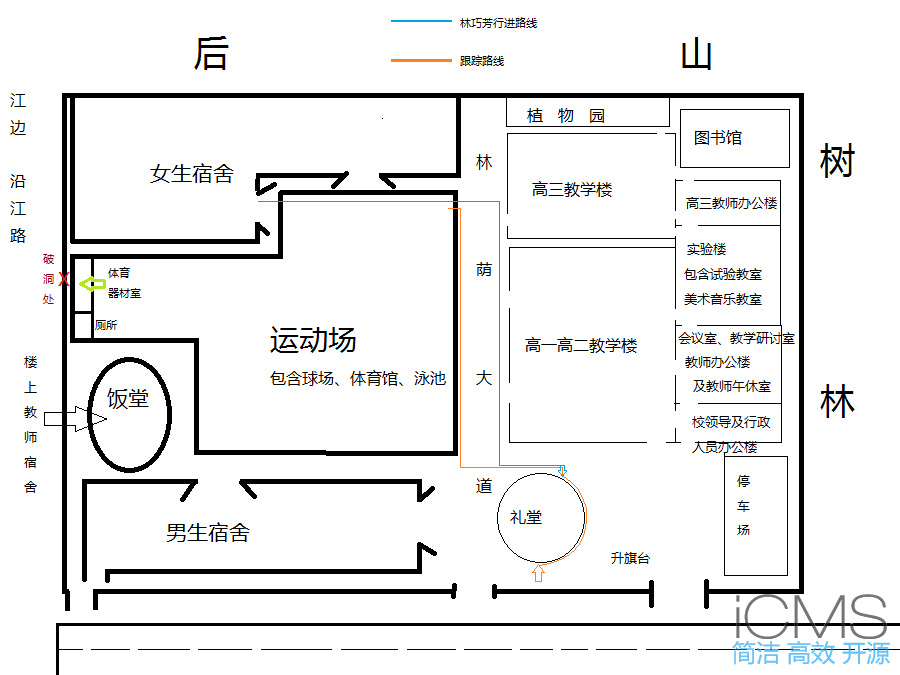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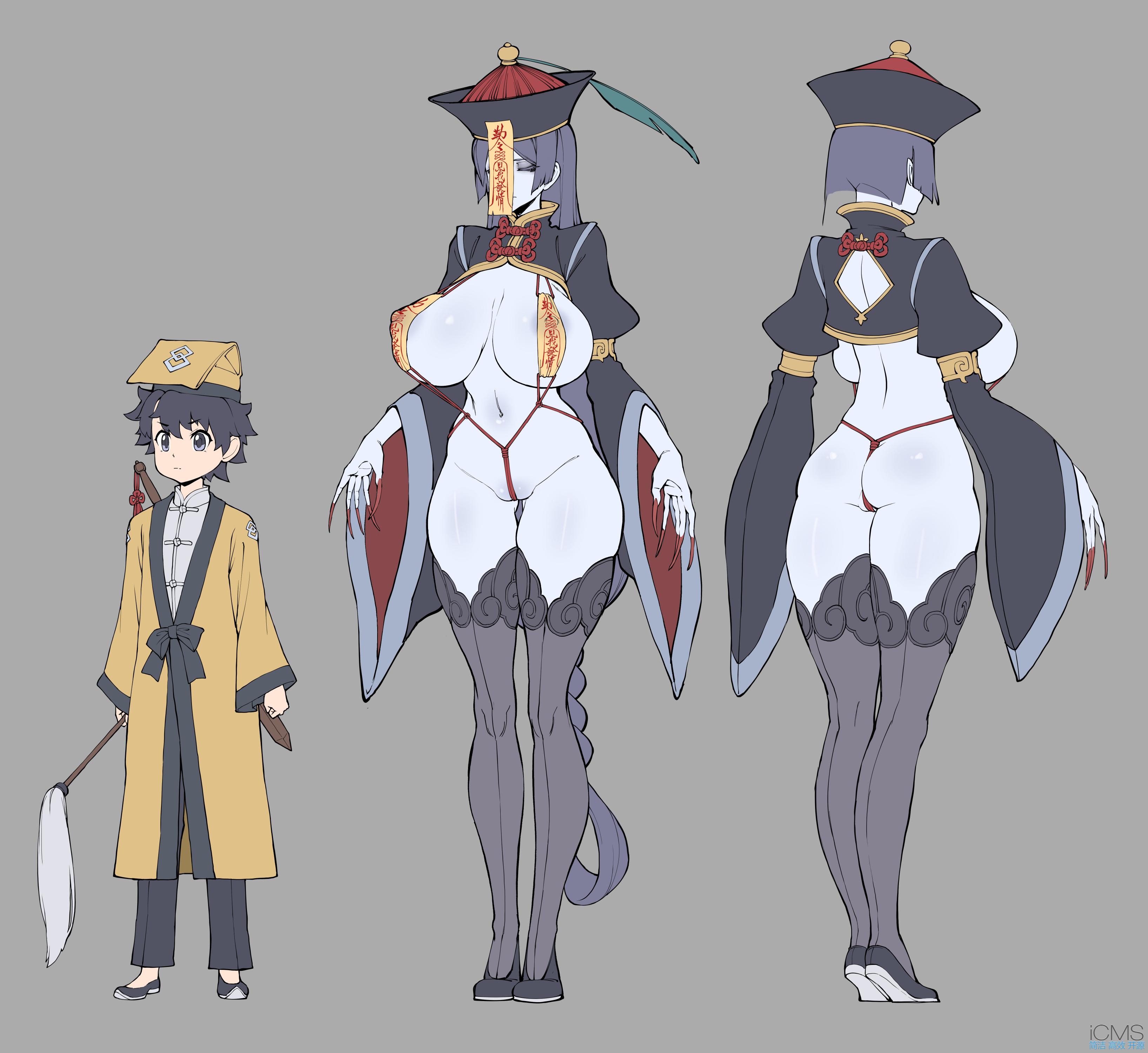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